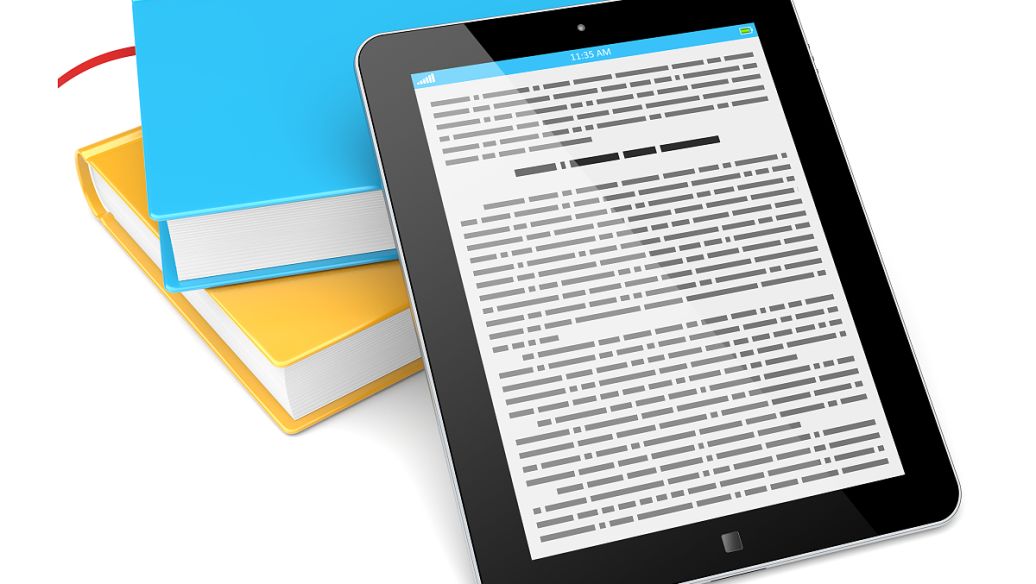长我十多岁的大哥曾说,人总是会死的,谁也不能例外。他笑容温柔,嗓音温润,总爱抚着我的头,像玩笑般的讲着此类话让我不知所云,只能见他在昏暗的黄沙之地咯咯直笑。
大哥笑声极为爽朗,性格也完全不像二哥那般阴沉,他有事没事总会带着我们走过村子的大街小巷,细数村内的名物,好似要将村子的一物一景刻在脑子里。
然后他奔赴了战场。
再然后,我就想起了他的话。
人总是会死的,谁也不能例外!
大哥的死讯是由村子的首领亲自告诉我们的,他那日一身黑衣,满眼藏不住的萧瑟。他是我们的表叔,父亲的幼弟,他平时和蔼可亲,我们全不见他战斗时的威风。可我就是欢喜他,即使他总喜欢拍着我的头,说我听不懂的话。但表叔从不会对我们说谎,也从不会隐瞒。
大哥死了,尸首全无。二哥紧抿双唇垂丧着头,谁也瞧不见他的神情。我站在他的边上,伸手扯住表叔的斗篷,问。
大哥真的死了吗?
回答我的不是表叔,而是二哥,他扯着嗓子大吼,我几乎看见了他眼中迸出的水光。
你再也见不到大哥了。
二哥用我最容易理解的话,告诉我什么叫死。我听完便哇哇哭叫起来,二哥拥着我,表叔蹲下身子拥着我们,我清晰地听见了二哥喉咙中的哽咽。于是,我哭得更大声,更悲伤。因为在村子里,唯有孩子才有放声大哭的权利。
因为……
在我出生那年,战争爆发了。
这是忍界的第二次战争,距离一战大约十年有余,一战之前,战争是忍者的家常便饭。在彼此因战斗衰弱的同时,战争的范围逐渐缩小,英雄则出于乱世。乱世之后,英雄多出,那也只是别人家的英雄,就像我的表叔。
表叔说,像现在这种有意发起的战争,可要比乱世残忍得多。我不明他的意思,只随着他站在村子的最高处,瞧着那些裹着皮革硬布的村人在诸多送别之语中离村。
然后,远方的天际便被浓墨染成了片,杀声不止。
表叔指着村子最西边的天空,那里响着轰鸣雷声,却不见电光闪烁。仿若能听得到呜鸣声从那边传来,我紧攥着表叔的斗篷,满眼都是恐惧。表叔蹲下身子,脸上笑容依旧慈爱,他说。大哥就在那里,二哥也会在那里,而我也将会在那里。他神情哀怯,眼中流转着粼光,好似下一秒那粼光便会闪落在脚下的寸寸黄沙之上。
大哥笑声极为爽朗,性格也完全不像二哥那般阴沉,他有事没事总会带着我们走过村子的大街小巷,细数村内的名物,好似要将村子的一物一景刻在脑子里。
然后他奔赴了战场。
再然后,我就想起了他的话。
人总是会死的,谁也不能例外!
大哥的死讯是由村子的首领亲自告诉我们的,他那日一身黑衣,满眼藏不住的萧瑟。他是我们的表叔,父亲的幼弟,他平时和蔼可亲,我们全不见他战斗时的威风。可我就是欢喜他,即使他总喜欢拍着我的头,说我听不懂的话。但表叔从不会对我们说谎,也从不会隐瞒。
大哥死了,尸首全无。二哥紧抿双唇垂丧着头,谁也瞧不见他的神情。我站在他的边上,伸手扯住表叔的斗篷,问。
大哥真的死了吗?
回答我的不是表叔,而是二哥,他扯着嗓子大吼,我几乎看见了他眼中迸出的水光。
你再也见不到大哥了。
二哥用我最容易理解的话,告诉我什么叫死。我听完便哇哇哭叫起来,二哥拥着我,表叔蹲下身子拥着我们,我清晰地听见了二哥喉咙中的哽咽。于是,我哭得更大声,更悲伤。因为在村子里,唯有孩子才有放声大哭的权利。
因为……
在我出生那年,战争爆发了。
这是忍界的第二次战争,距离一战大约十年有余,一战之前,战争是忍者的家常便饭。在彼此因战斗衰弱的同时,战争的范围逐渐缩小,英雄则出于乱世。乱世之后,英雄多出,那也只是别人家的英雄,就像我的表叔。
表叔说,像现在这种有意发起的战争,可要比乱世残忍得多。我不明他的意思,只随着他站在村子的最高处,瞧着那些裹着皮革硬布的村人在诸多送别之语中离村。
然后,远方的天际便被浓墨染成了片,杀声不止。
表叔指着村子最西边的天空,那里响着轰鸣雷声,却不见电光闪烁。仿若能听得到呜鸣声从那边传来,我紧攥着表叔的斗篷,满眼都是恐惧。表叔蹲下身子,脸上笑容依旧慈爱,他说。大哥就在那里,二哥也会在那里,而我也将会在那里。他神情哀怯,眼中流转着粼光,好似下一秒那粼光便会闪落在脚下的寸寸黄沙之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