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章
泥墙斑驳,垃圾散乱,杆顶的电线黑污横七竖八,墙壁那一线天空,支离破碎,这里是方无人问津的世界。
横倒的破自行车,后轮兀自转着,链条摩擦出吱嗝声,转速越来越慢。
前轮压着一条腿,裹在水洗磨白的仔裤里,瘦的紧,深褐色的湿迹晕开,快的像粗糙面巾纸上滴入的清水。
阿信混沌间觉得胸口闷的厉害,吸气跟吞刀子似的,气管心脏都绞碎,他形容不出那种疼痛,部分地方油浇火燎,可心口和手脚,却越发冰冷,冻成冰棍了似的,屈伸指节都做不到。
他睁不开眼,只感到眼缝处一线灰败的光,疼痛范围太广,而他也记不起,是眼皮被打肿了,还是自己没力气了。
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疲倦,就想一闭眼,黑暗一片。
可他非要活受罪,撑着那丝岌岌可危的精神,感受肉体重创带来的痛苦。
他才二十四,没谈过恋爱,很多地方没去过,很多美食没尝过,没见过爸妈,没青梅竹马,最可惜的是,他喜欢的人,没有喜欢过他……他不想死,可阿信知道,他活不了了。
那一枪从后心洞穿胸口的时候,他清晰的感觉到死亡的阴影罩下,心脏有一瞬间跳到极限,甚至能感受到复杂的人体器官肌肉紧缩颤动的频率,浑身如置冰窖。
眼前突如其来那阵浓黑没有缓缓褪去,他瞬间就昏厥了,连带着在路上捡来的破自行车,一同歪倒在地。
意识再回归,就成了这副元神出窍、植物人节奏的死德性。
胸口尖锐的疼,有压迫窒息的厉害,阿信脑子生锈不灵光,逻辑乱七八糟,想了半天才捋清楚,他左拐之后要去找侯勇,沿路气喘如牛的疯跑,气息放荡不羁,速度却不上档,后头追着他的三个马拉松之神附体一样,撒丫跑的恨不能在身后扬起一道浓烟,很快就给他一脚踹翻摁倒在灰里。
他们问他侯勇在哪里,阿信抱着头说不知道,循环该过程几遍,就被按着一顿狂揍,鼻子眼照打不误,于是他很快就成了一猪头。
虽说双拳难敌四手,可阿信裤兜里有刀片,加上他曾经当过贼,手指灵活度非比寻常,那浑实胖子一拳头捶下来,他捏了刀片瞅准就朝他腕动脉来了一刀,那胖子刚刚运动激烈,刃口处瞬间就成喷涌状飙出一捧血,温热腥气含氧量还高,出血量将两同伙吓得懵了一瞬。
阿信一鼓作气乱划一通,三个都见了血,刀片锋利,口子又细又深,三人有些慌,阿信一脚猛踩上对面一人裆部,那人惨叫一声捂住那处,倒在地上打起了滚。
阿信又连将另二人推个大马趴,拔腿就跑,他在狂奔的路上看见一辆破烂自行车,后胎瘪瘪没气,他还是大喜,一屁股上去当抹布,蹬着脚蹬玩命狂踩。
两轮子实在比两条短腿强不少,巷口又多,他一个拐弯窜进去,被他推倒那两个爬起来,弄了下伤口再去追他,就没人影了。
阿信见没人追,就蹬着烂车在巷子里须溜,一路找侯勇。
他在一尾巷口,看见武平的心腹猴子带着人行色匆匆的张望搜寻,他就以为想弄死侯勇的是武平,隔着一条巷子小心的辍着。
顾头没心力顾尾,不知被谁在背后开了一枪,只感觉到人数不少,脚步杂乱,没看清人,就晕过去了。
胸口中了枪,那腿上怎么他妈也这么疼?
身下的水泥地润了血,在阿信两臂旁晕开一团不规则的圆,左边大腿裤子湿透,弹孔那处深黑一点,从上方俯视的角度,他就像一个面如白纸的死人,躺在炼金术士勾画的怪异符咒里,进行某种祭祀仪式——如果身上没压着一辆碍事自行车的话。
阿信呕出一口带着内脏碎片的血沫,糊了一下巴,他想,勇哥不知道安全了没——
还有,文东,我他妈真的……很想亲眼看看你,手指是不是真的在!
泥墙斑驳,垃圾散乱,杆顶的电线黑污横七竖八,墙壁那一线天空,支离破碎,这里是方无人问津的世界。
横倒的破自行车,后轮兀自转着,链条摩擦出吱嗝声,转速越来越慢。
前轮压着一条腿,裹在水洗磨白的仔裤里,瘦的紧,深褐色的湿迹晕开,快的像粗糙面巾纸上滴入的清水。
阿信混沌间觉得胸口闷的厉害,吸气跟吞刀子似的,气管心脏都绞碎,他形容不出那种疼痛,部分地方油浇火燎,可心口和手脚,却越发冰冷,冻成冰棍了似的,屈伸指节都做不到。
他睁不开眼,只感到眼缝处一线灰败的光,疼痛范围太广,而他也记不起,是眼皮被打肿了,还是自己没力气了。
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疲倦,就想一闭眼,黑暗一片。
可他非要活受罪,撑着那丝岌岌可危的精神,感受肉体重创带来的痛苦。
他才二十四,没谈过恋爱,很多地方没去过,很多美食没尝过,没见过爸妈,没青梅竹马,最可惜的是,他喜欢的人,没有喜欢过他……他不想死,可阿信知道,他活不了了。
那一枪从后心洞穿胸口的时候,他清晰的感觉到死亡的阴影罩下,心脏有一瞬间跳到极限,甚至能感受到复杂的人体器官肌肉紧缩颤动的频率,浑身如置冰窖。
眼前突如其来那阵浓黑没有缓缓褪去,他瞬间就昏厥了,连带着在路上捡来的破自行车,一同歪倒在地。
意识再回归,就成了这副元神出窍、植物人节奏的死德性。
胸口尖锐的疼,有压迫窒息的厉害,阿信脑子生锈不灵光,逻辑乱七八糟,想了半天才捋清楚,他左拐之后要去找侯勇,沿路气喘如牛的疯跑,气息放荡不羁,速度却不上档,后头追着他的三个马拉松之神附体一样,撒丫跑的恨不能在身后扬起一道浓烟,很快就给他一脚踹翻摁倒在灰里。
他们问他侯勇在哪里,阿信抱着头说不知道,循环该过程几遍,就被按着一顿狂揍,鼻子眼照打不误,于是他很快就成了一猪头。
虽说双拳难敌四手,可阿信裤兜里有刀片,加上他曾经当过贼,手指灵活度非比寻常,那浑实胖子一拳头捶下来,他捏了刀片瞅准就朝他腕动脉来了一刀,那胖子刚刚运动激烈,刃口处瞬间就成喷涌状飙出一捧血,温热腥气含氧量还高,出血量将两同伙吓得懵了一瞬。
阿信一鼓作气乱划一通,三个都见了血,刀片锋利,口子又细又深,三人有些慌,阿信一脚猛踩上对面一人裆部,那人惨叫一声捂住那处,倒在地上打起了滚。
阿信又连将另二人推个大马趴,拔腿就跑,他在狂奔的路上看见一辆破烂自行车,后胎瘪瘪没气,他还是大喜,一屁股上去当抹布,蹬着脚蹬玩命狂踩。
两轮子实在比两条短腿强不少,巷口又多,他一个拐弯窜进去,被他推倒那两个爬起来,弄了下伤口再去追他,就没人影了。
阿信见没人追,就蹬着烂车在巷子里须溜,一路找侯勇。
他在一尾巷口,看见武平的心腹猴子带着人行色匆匆的张望搜寻,他就以为想弄死侯勇的是武平,隔着一条巷子小心的辍着。
顾头没心力顾尾,不知被谁在背后开了一枪,只感觉到人数不少,脚步杂乱,没看清人,就晕过去了。
胸口中了枪,那腿上怎么他妈也这么疼?
身下的水泥地润了血,在阿信两臂旁晕开一团不规则的圆,左边大腿裤子湿透,弹孔那处深黑一点,从上方俯视的角度,他就像一个面如白纸的死人,躺在炼金术士勾画的怪异符咒里,进行某种祭祀仪式——如果身上没压着一辆碍事自行车的话。
阿信呕出一口带着内脏碎片的血沫,糊了一下巴,他想,勇哥不知道安全了没——
还有,文东,我他妈真的……很想亲眼看看你,手指是不是真的在!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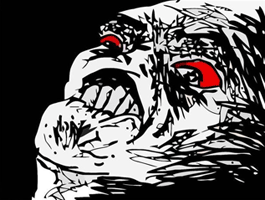



 (这样不是显得我很无知么摔!!!)
(这样不是显得我很无知么摔!!!) 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