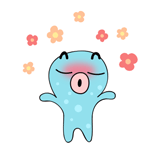霍建华吧 关注:1,487,562贴子:27,931,812
引文:
简洁古朴的院落,曲廊环绕亭院,缀以花木石峰,从曲廊空窗望去这院落俨然已成一幅意蕴丰富的画。一大片的梅花树与天相接,更显这院落的脱俗之美感。她踮脚一跃至屋顶,眼神涣散而无光。她不知道她想要做什么,是漠然俯视这梅花海,还是拔剑毁了眼前一切。
白里透粉的梅花树下,一男子慵懒的倚树而站,默默不语,他身着一身不起眼的紫,本是一头的散发被一根紫色发带箍的一丝不紊,寒风扫过,他长袍的下摆从腰间半剥离,飞起来就像蝴蝶的翅膀,优雅夺目。在她与他对视那一刻,他于她莞尔一笑。
那个笑,璀璨夺目。太耀眼。她想靠近一点,一点点,看仔细些。
于是,她运轻功至那一身紫衣前。紫衣男子笑着轻启唇唤她的名字,她微楞了一下,身子却不容大脑反应,剑出鞘就往前面刺过去,直直插入他的心脏。
血溅至她白色的衣袍,应是触目惊心,她却没有任何表情,毫不在意作态,松开了握剑柄的手。紫衣错愕了一会,便恢复至笑意满面,他朝她笑的如白梅盛开,像从未有剑伤着他。他握住剑刃的手已溢满了鲜血,可他不能让剑再深一分。
她赛雪欺霜的站于紫衣男子身前。一阵风吹过,梅花徐徐飘落漫天,遮盖住他们对望的视线。
简洁古朴的院落,曲廊环绕亭院,缀以花木石峰,从曲廊空窗望去这院落俨然已成一幅意蕴丰富的画。一大片的梅花树与天相接,更显这院落的脱俗之美感。她踮脚一跃至屋顶,眼神涣散而无光。她不知道她想要做什么,是漠然俯视这梅花海,还是拔剑毁了眼前一切。
白里透粉的梅花树下,一男子慵懒的倚树而站,默默不语,他身着一身不起眼的紫,本是一头的散发被一根紫色发带箍的一丝不紊,寒风扫过,他长袍的下摆从腰间半剥离,飞起来就像蝴蝶的翅膀,优雅夺目。在她与他对视那一刻,他于她莞尔一笑。
那个笑,璀璨夺目。太耀眼。她想靠近一点,一点点,看仔细些。
于是,她运轻功至那一身紫衣前。紫衣男子笑着轻启唇唤她的名字,她微楞了一下,身子却不容大脑反应,剑出鞘就往前面刺过去,直直插入他的心脏。
血溅至她白色的衣袍,应是触目惊心,她却没有任何表情,毫不在意作态,松开了握剑柄的手。紫衣错愕了一会,便恢复至笑意满面,他朝她笑的如白梅盛开,像从未有剑伤着他。他握住剑刃的手已溢满了鲜血,可他不能让剑再深一分。
她赛雪欺霜的站于紫衣男子身前。一阵风吹过,梅花徐徐飘落漫天,遮盖住他们对望的视线。
3
夜幕终是替了晚霞,上映星月之歌。夜空似藏青色的帷幕,点缀着闪闪繁星,让人不由深深地沉醉。
我们在周围捡了一些柴,就地生起火,喜乐滋滋的烤起黎大哥抓的几只野山鸡。
我打心眼里觉得我同胡大哥、黎大哥太过于相熟,第二次见面就感觉如同一起生活了好多年那般亲近。要不是黎大哥说他们之前是在京师做锦衣卫,这次出差做任务才到四川小住,我当真会认定他们是我失忆之前就要好的人。
黎大哥还是如二候前我见他那般,话不多,仅替我烤着山鸡,端着酒往嘴里送。大块头告诉我,在未见面的二候里,他们去了趟姑苏,寻了寻故人,可惜故人已不在姑苏城,了无音讯。
大块头说完,长叹了一口气,抢过歌先生的酒,牛饮了小半壶。
对于没有记忆的我,正反是不懂这种‘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’的感情。
我是嫉妒一切有记忆的人,在道观里嫉妒苏妙,出了道观嫉妒胡大哥,眼下更是嫉妒他们这个故人。若是哪一天黎大哥和大块头就此回京师,一去不返,他们会不会同眼下惦记故人一样惦记着我呢。
我垂下头,自嘲的笑了笑。这般闻其手里的烤鸡也变了味。
“飞燕,近来睡的可是安稳吗?”黎大哥满脸关心的问道,顺势接过我手里凉了的烤山鸡,体贴的递给我一只还冒着热气的。
二候前我把我总是做噩梦一事同黎大哥道了,万事皆通的黎大哥便送予我一只香囊,道是香囊在旁能有凝神定气之功用。
可十日下来,噩梦是减少了,换做我摸不着头脑的怪梦。到也不皆是杀人的梦,还有些甜蜜的,热闹的。像是一群梦里熟悉的人吵吵嚷嚷围着火炉吃火锅,又像是女子倚在男子怀里听他吹笛。
“嗯,睡的沉。”大整晚的尽做梦白天自然睡的沉,我咬了几口烤鸡,腹诽着。
我着实是不想再让黎大哥替我睡眠这方面操心。明明他面色比我还憔悴,比分别前又瘦了一些,光看他这个样子,就觉得心里扎着疼。
他笑着喝了一口酒。“那便好。”
看到黎大哥在笑,我就有点得意忘形,想再做些甚么,让他更高兴一些。
“黎大哥,你上次教我的几招剑法,我都有练习,武的很好。”说着我就起身捡了一根树枝比划给他看。
那是我吃晚饭后必备的练习,我想等下次见着黎大哥的时候,同他展现出最好的一面。想看他笑逐颜开夸我的样子。连同苏妙都以为我开窍了道我勤勉。
虽仍是无法握住剑柄,但用小树枝练习剑术,还是绰绰有余顺风顺水的。
我反反复复把黎大哥教我的两招端正的演示了很多遍,也不见黎大哥有反应。直至大块头倏忽跳出来,也捡了一根树枝同我比划,黎大哥才青着脸站起来。
我原是按着黎大哥教我的招式出,后被大块头的招式逼得乱成一团。手不由自主地竟随着大块头剑法的变化动了起来。见招拆招的巧妙,却不是峨眉剑法,似是同梦里的剑术一样。
我惊呆了,等我反应过来时,我竟把大块头手中的树枝给打掉落地。顺着自己笔直的胳膊望过去,傻傻地看着剑尖的尽头,我手里的树枝正抵着黎大哥的胸口。
这下真同梦境一模一样了。
若说我不是有意而为之,是我跳进峨眉的天池也洗不清了。
黎大哥面无表情的颔首看着抵着胸口的树枝,眼里的墨色深不见底。那种陌生的感觉好似与他在山坡初见时,我正对着夕阳哭的起劲,他闯入了我模糊的眼帘。黎大哥涣散着眼,领着酒壶晃步而来。晚霞打在他脸上是暖色的黄,而他的脸正与之相反,不带一丝热度的刻在我心上,全然是冷漠。
我赶忙扔了树枝,心急如焚的张着嘴,半天发不出一个音节。我想同他辩解,方才我是被鬼附身了,是脑子被进水了,是被下蛊毒了。正反不是我本意啊。
看他烟波里的光沉下去,我急的红了眼,瞪着旁边很是悠哉吃着烤山鸡,满脸写着‘与我无关’的大块头,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我想啊,干脆撂挑子同他道,大不了我们不要见面了,本就是路人的关系嘛,江湖再见也不尴尬啊。
我抽了抽鼻子,可我不舍得啊。连想到这么说会惹黎大哥不高兴,就那么不舍。想到他蹙着眉的样子,就那么不舍。
我来不及想这些个不舍是为甚,就被一个暖怀给拥的透彻。整个人愣在原地,双手也不知该如何安放,只得规规矩矩的放至两侧。
“飞燕,是我不好,吓着你了。”直至黎大哥低哑的声音从头上传入我耳,我才真真切切感到是黎大哥抱住了我,是我只见了一面就惦念不已的黎大哥。鼻端嗅到他身上淡淡的药香,慢慢的,脸上像在炊火上烧的烤鸡一般热乎乎的。
“是……是……是我的错,明明连树枝都掌控不了,还妄想武剑。”我自我检讨说的小声。
黎大哥从怀里微微拉开我,眸子柔了柔,道。“你已经做的很好了。”
我红着脸,生硬的点了点头,刚想学着戏本子小家碧玉说些情话,便听突然放下烤鸡的胡大哥开了口。“离歌——不是啊老离”
这称谓才出口,大块头就被黎大哥瞪得握烤鸡的手抖了抖。
“不是我成心要打断你们,飞燕的伤口渗出血了,要不要快点送她回去换药啊?”
我望了望肩膀处土黄色的道袍被血染成了别的颜色,这才意识到刚刚武树枝的时候太用力,生生的把伤口给扯裂了。
黎大哥蹙着眉,随手扯下自己的衣角,撕成条,小心翼翼的替我简单包扎了一下,包扎完不由分说的就立刻赶我回山上。
大块头本是想一同的,被我和黎大哥瞪他的两道目光给生生逼退,老实巴巴的继续啃着他的烧鸡。
本着黎大哥抱了我,就愿意同我一辈子亲近的意愿。回峨眉的路上,我拽着他的袖子,厚着脸皮问了他好些问题。
“方才胡大哥唤你黎歌,你当真叫这个名字?”
他举着火把,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,长长‘嗯’了一声,且调子上扬。
黎歌,黎歌,这个名字约莫是他爹娘遭遇的离别太多了,才有情有感的取于他这名。想来,我的名字与黎大哥的名字默契至极。谢飞燕,伯劳飞燕,也作离别之解。师姐说我这名字注定克父克母,孤独一生。那时还想同她们作命拼,现想起,我倒愿意同黎歌出一处,一块孤独一生的。
可两个人,又怎么能叫做孤独呢?
“黎大哥,我以后……唔……我以后是否能唤你作‘歌先生’啊?”我犹犹豫豫开了口,脑子里馄饨中有个小姑娘扬着嗓子道‘那我以后就唤他歌先生吧’另外一个人笑着回道‘歌先生,好听’
黎大哥顿了顿步,手里的火把斜了斜。“怎么忽然想起这个?”树林里太暗,我看不清旁边黎大哥的表情,只好咽了咽口水,道“好听啊,而且黎大哥你也算教了我剑法,当得起先生这个称呼。”
“随便你吧。”他话中带笑,我胆子不觉又肥了一圈。
我又问歌先生,有妻室与否。
他静默,思虑了良久才回道,有。
我心里的小火苗霎时被扑灭,沮丧的不想说,不想动。先生似以为我伤口不舒适,举着火把照亮我的脸,忧心忡忡的回头望我。看我心如死灰的摸样,他一时竟眸子弯成月牙,嘴角止不住的扬起,道。‘曾有,我妻子已安于地下七年了。’
我前一秒被熄灭的小火苗,即刻燎了原。
我边扬着脸冲他安慰的笑,边不矜不盈的挽过他闲着的那只胳膊。稍稍拽开袖口,一个迥殊闪眼的手链就露出了一角。说是手链也过分,只是一颗珍珠用红绳子攒起来罢。
歌先生见我出神的盯着,便不动声色的用衣袖盖住了链子。
我猜这根链子定是他已故的娘子送予他的,他才如此宝贝。想着,我怏怏不乐的继续同他走。
歌先生于后半路一直在反复嘱咐我,在他们回京师复命,不在峨眉后山的这段日子里,万不能不经师父允许逃出来游玩,又同我反复道,伤口要勤换药,不要多动武。
这很难不让我想到,我跪在祠堂里罚抄佛经时,师父的唠叨。真真是如出一辙的。
说起,比起师姐的刻薄,同辈的排挤,我更享受于这种唠叨的。那是出于真心关切的叨念。
在快走到有师姐看守的小后门时,他这才又作沉闷状,随意的作了个揖来向我道别。
想到又要十天半月才能相见,我又不念及矜持为何物。在他移步之前,我一把抱住他的胳膊。
“早些回来……我会惦念你…你…和胡大哥的,等你回来烤山猪肉吧。”
他噗嗤一声,笑的开怀,眉开眼笑的伸另一只手来捏我的脸。“十天后老地方见。”
我想,我没告诉过先生,他温柔冲我笑的时,我的怦然心动。亦没告诉过他,他每每用关切的目光看我时,我的忧虑忐忑。
因为他关切我时,于我的感觉,同梦里我出剑伤的那个紫衣男子给我的感觉,一模一样。
这是我第一次害怕起我的过去同歌先生有牵扯,自不是最后一次。
夜幕终是替了晚霞,上映星月之歌。夜空似藏青色的帷幕,点缀着闪闪繁星,让人不由深深地沉醉。
我们在周围捡了一些柴,就地生起火,喜乐滋滋的烤起黎大哥抓的几只野山鸡。
我打心眼里觉得我同胡大哥、黎大哥太过于相熟,第二次见面就感觉如同一起生活了好多年那般亲近。要不是黎大哥说他们之前是在京师做锦衣卫,这次出差做任务才到四川小住,我当真会认定他们是我失忆之前就要好的人。
黎大哥还是如二候前我见他那般,话不多,仅替我烤着山鸡,端着酒往嘴里送。大块头告诉我,在未见面的二候里,他们去了趟姑苏,寻了寻故人,可惜故人已不在姑苏城,了无音讯。
大块头说完,长叹了一口气,抢过歌先生的酒,牛饮了小半壶。
对于没有记忆的我,正反是不懂这种‘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’的感情。
我是嫉妒一切有记忆的人,在道观里嫉妒苏妙,出了道观嫉妒胡大哥,眼下更是嫉妒他们这个故人。若是哪一天黎大哥和大块头就此回京师,一去不返,他们会不会同眼下惦记故人一样惦记着我呢。
我垂下头,自嘲的笑了笑。这般闻其手里的烤鸡也变了味。
“飞燕,近来睡的可是安稳吗?”黎大哥满脸关心的问道,顺势接过我手里凉了的烤山鸡,体贴的递给我一只还冒着热气的。
二候前我把我总是做噩梦一事同黎大哥道了,万事皆通的黎大哥便送予我一只香囊,道是香囊在旁能有凝神定气之功用。
可十日下来,噩梦是减少了,换做我摸不着头脑的怪梦。到也不皆是杀人的梦,还有些甜蜜的,热闹的。像是一群梦里熟悉的人吵吵嚷嚷围着火炉吃火锅,又像是女子倚在男子怀里听他吹笛。
“嗯,睡的沉。”大整晚的尽做梦白天自然睡的沉,我咬了几口烤鸡,腹诽着。
我着实是不想再让黎大哥替我睡眠这方面操心。明明他面色比我还憔悴,比分别前又瘦了一些,光看他这个样子,就觉得心里扎着疼。
他笑着喝了一口酒。“那便好。”
看到黎大哥在笑,我就有点得意忘形,想再做些甚么,让他更高兴一些。
“黎大哥,你上次教我的几招剑法,我都有练习,武的很好。”说着我就起身捡了一根树枝比划给他看。
那是我吃晚饭后必备的练习,我想等下次见着黎大哥的时候,同他展现出最好的一面。想看他笑逐颜开夸我的样子。连同苏妙都以为我开窍了道我勤勉。
虽仍是无法握住剑柄,但用小树枝练习剑术,还是绰绰有余顺风顺水的。
我反反复复把黎大哥教我的两招端正的演示了很多遍,也不见黎大哥有反应。直至大块头倏忽跳出来,也捡了一根树枝同我比划,黎大哥才青着脸站起来。
我原是按着黎大哥教我的招式出,后被大块头的招式逼得乱成一团。手不由自主地竟随着大块头剑法的变化动了起来。见招拆招的巧妙,却不是峨眉剑法,似是同梦里的剑术一样。
我惊呆了,等我反应过来时,我竟把大块头手中的树枝给打掉落地。顺着自己笔直的胳膊望过去,傻傻地看着剑尖的尽头,我手里的树枝正抵着黎大哥的胸口。
这下真同梦境一模一样了。
若说我不是有意而为之,是我跳进峨眉的天池也洗不清了。
黎大哥面无表情的颔首看着抵着胸口的树枝,眼里的墨色深不见底。那种陌生的感觉好似与他在山坡初见时,我正对着夕阳哭的起劲,他闯入了我模糊的眼帘。黎大哥涣散着眼,领着酒壶晃步而来。晚霞打在他脸上是暖色的黄,而他的脸正与之相反,不带一丝热度的刻在我心上,全然是冷漠。
我赶忙扔了树枝,心急如焚的张着嘴,半天发不出一个音节。我想同他辩解,方才我是被鬼附身了,是脑子被进水了,是被下蛊毒了。正反不是我本意啊。
看他烟波里的光沉下去,我急的红了眼,瞪着旁边很是悠哉吃着烤山鸡,满脸写着‘与我无关’的大块头,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我想啊,干脆撂挑子同他道,大不了我们不要见面了,本就是路人的关系嘛,江湖再见也不尴尬啊。
我抽了抽鼻子,可我不舍得啊。连想到这么说会惹黎大哥不高兴,就那么不舍。想到他蹙着眉的样子,就那么不舍。
我来不及想这些个不舍是为甚,就被一个暖怀给拥的透彻。整个人愣在原地,双手也不知该如何安放,只得规规矩矩的放至两侧。
“飞燕,是我不好,吓着你了。”直至黎大哥低哑的声音从头上传入我耳,我才真真切切感到是黎大哥抱住了我,是我只见了一面就惦念不已的黎大哥。鼻端嗅到他身上淡淡的药香,慢慢的,脸上像在炊火上烧的烤鸡一般热乎乎的。
“是……是……是我的错,明明连树枝都掌控不了,还妄想武剑。”我自我检讨说的小声。
黎大哥从怀里微微拉开我,眸子柔了柔,道。“你已经做的很好了。”
我红着脸,生硬的点了点头,刚想学着戏本子小家碧玉说些情话,便听突然放下烤鸡的胡大哥开了口。“离歌——不是啊老离”
这称谓才出口,大块头就被黎大哥瞪得握烤鸡的手抖了抖。
“不是我成心要打断你们,飞燕的伤口渗出血了,要不要快点送她回去换药啊?”
我望了望肩膀处土黄色的道袍被血染成了别的颜色,这才意识到刚刚武树枝的时候太用力,生生的把伤口给扯裂了。
黎大哥蹙着眉,随手扯下自己的衣角,撕成条,小心翼翼的替我简单包扎了一下,包扎完不由分说的就立刻赶我回山上。
大块头本是想一同的,被我和黎大哥瞪他的两道目光给生生逼退,老实巴巴的继续啃着他的烧鸡。
本着黎大哥抱了我,就愿意同我一辈子亲近的意愿。回峨眉的路上,我拽着他的袖子,厚着脸皮问了他好些问题。
“方才胡大哥唤你黎歌,你当真叫这个名字?”
他举着火把,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,长长‘嗯’了一声,且调子上扬。
黎歌,黎歌,这个名字约莫是他爹娘遭遇的离别太多了,才有情有感的取于他这名。想来,我的名字与黎大哥的名字默契至极。谢飞燕,伯劳飞燕,也作离别之解。师姐说我这名字注定克父克母,孤独一生。那时还想同她们作命拼,现想起,我倒愿意同黎歌出一处,一块孤独一生的。
可两个人,又怎么能叫做孤独呢?
“黎大哥,我以后……唔……我以后是否能唤你作‘歌先生’啊?”我犹犹豫豫开了口,脑子里馄饨中有个小姑娘扬着嗓子道‘那我以后就唤他歌先生吧’另外一个人笑着回道‘歌先生,好听’
黎大哥顿了顿步,手里的火把斜了斜。“怎么忽然想起这个?”树林里太暗,我看不清旁边黎大哥的表情,只好咽了咽口水,道“好听啊,而且黎大哥你也算教了我剑法,当得起先生这个称呼。”
“随便你吧。”他话中带笑,我胆子不觉又肥了一圈。
我又问歌先生,有妻室与否。
他静默,思虑了良久才回道,有。
我心里的小火苗霎时被扑灭,沮丧的不想说,不想动。先生似以为我伤口不舒适,举着火把照亮我的脸,忧心忡忡的回头望我。看我心如死灰的摸样,他一时竟眸子弯成月牙,嘴角止不住的扬起,道。‘曾有,我妻子已安于地下七年了。’
我前一秒被熄灭的小火苗,即刻燎了原。
我边扬着脸冲他安慰的笑,边不矜不盈的挽过他闲着的那只胳膊。稍稍拽开袖口,一个迥殊闪眼的手链就露出了一角。说是手链也过分,只是一颗珍珠用红绳子攒起来罢。
歌先生见我出神的盯着,便不动声色的用衣袖盖住了链子。
我猜这根链子定是他已故的娘子送予他的,他才如此宝贝。想着,我怏怏不乐的继续同他走。
歌先生于后半路一直在反复嘱咐我,在他们回京师复命,不在峨眉后山的这段日子里,万不能不经师父允许逃出来游玩,又同我反复道,伤口要勤换药,不要多动武。
这很难不让我想到,我跪在祠堂里罚抄佛经时,师父的唠叨。真真是如出一辙的。
说起,比起师姐的刻薄,同辈的排挤,我更享受于这种唠叨的。那是出于真心关切的叨念。
在快走到有师姐看守的小后门时,他这才又作沉闷状,随意的作了个揖来向我道别。
想到又要十天半月才能相见,我又不念及矜持为何物。在他移步之前,我一把抱住他的胳膊。
“早些回来……我会惦念你…你…和胡大哥的,等你回来烤山猪肉吧。”
他噗嗤一声,笑的开怀,眉开眼笑的伸另一只手来捏我的脸。“十天后老地方见。”
我想,我没告诉过先生,他温柔冲我笑的时,我的怦然心动。亦没告诉过他,他每每用关切的目光看我时,我的忧虑忐忑。
因为他关切我时,于我的感觉,同梦里我出剑伤的那个紫衣男子给我的感觉,一模一样。
这是我第一次害怕起我的过去同歌先生有牵扯,自不是最后一次。






 了
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