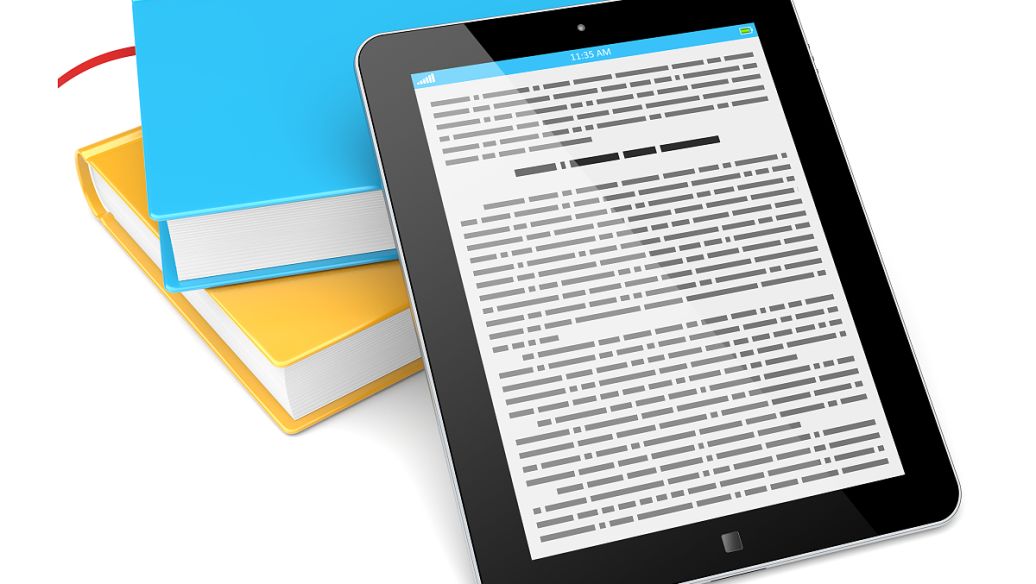小说吧 关注:6,992,610贴子:37,646,771
〔启〕
一
入夜后下起了暴雨,一直不停。屋顶漏了,牢房里滴滴答答地下小雨,当作床垫的稻草一股霉味儿,引得囚犯们连声地骂娘。狱卒在这种坏天气里也没好气,不耐烦了就进来挥舞铁棍敲打铁栏杆,大声地喝骂。几次三番囚犯们也不骂娘了,知道抱怨也没用,反正在漏水的牢房里也睡不着,于是隔着铁栏杆三三两两地凑一起说闲话聊女人,居然有酒肆般的热闹。
黑衣的年轻人支着下巴望向窗外,修长的手指随着嘀嗒的雨声敲打膝盖,他的囚衣与其他人不同看起来更加厚实一些,是特意加了棉的。隔壁的老囚犯敲敲铁栏,递过一盘干瘪的花生米,冲年轻人呲牙一笑,年轻人愣了下,也笑笑,拈了两粒放进嘴里嚼。这老囚犯在这关了许多年,跟狱卒也打的好关系,总有些平日罪犯们吃不到的东西,据说他刚关进来的时候还很年轻,现在已经老的快死掉了。
这座监狱名字起得森严可怖,其实什么人都关,豪门里惹出是非的淫娃妖妇、市井里打架杀人的贩夫走卒、乃至一些犯了事的低阶的官员,都可能往这里扔。不过这里也是南淮城里防备最森严的监狱,关在这里的人犯的事儿都不小,隔几天就砍几个,牢房空了又填满,犯人流水样地换。当然也有像老汉这样的例外。
“说起来老哥儿你是犯了什么事儿?”年轻人捏着手心里的两枚石子儿抛了抛。
“假造金票,是杀头的罪。”对面的老囚犯倒也不很沮丧,答得很是坦然。 “假造了多少?”
“也就二十万金铢。”
年轻人愣了一下,笑出声来:“难怪是杀头的罪,你假造的金票可以买半条紫梁大街了。”
“那您是犯了什么事儿?您可是帝都大名鼎鼎的大将军,能沦落到这里来,犯的事儿不会小。”老囚犯反问,他们这些人关得久,跟外面不通消息。
年轻人抓了抓头:“说起来被抓到了把柄的事儿也就是私下里调动军队。” “调动军队?调动了多少人呐?”老囚犯追着不放。
“也就三四万人。”年轻人学他的口气。 “难怪是杀头的罪,你私下调动的人能把一国给打下来了。”老囚犯得意洋洋的报复。
两人一起笑了起来,看起来对于彼此要被杀头这个事情倒有几分欢悦。 “其实我觉得我还算运气的。”老囚犯说。 “你是说没判磔刑算运气?”
“不是,”老囚犯说,“反正我没家人,死了就死了,没什么牵挂的,这就是运气。早知道造它两百万金铢的票子出来,也还是砍头吧?”
一
入夜后下起了暴雨,一直不停。屋顶漏了,牢房里滴滴答答地下小雨,当作床垫的稻草一股霉味儿,引得囚犯们连声地骂娘。狱卒在这种坏天气里也没好气,不耐烦了就进来挥舞铁棍敲打铁栏杆,大声地喝骂。几次三番囚犯们也不骂娘了,知道抱怨也没用,反正在漏水的牢房里也睡不着,于是隔着铁栏杆三三两两地凑一起说闲话聊女人,居然有酒肆般的热闹。
黑衣的年轻人支着下巴望向窗外,修长的手指随着嘀嗒的雨声敲打膝盖,他的囚衣与其他人不同看起来更加厚实一些,是特意加了棉的。隔壁的老囚犯敲敲铁栏,递过一盘干瘪的花生米,冲年轻人呲牙一笑,年轻人愣了下,也笑笑,拈了两粒放进嘴里嚼。这老囚犯在这关了许多年,跟狱卒也打的好关系,总有些平日罪犯们吃不到的东西,据说他刚关进来的时候还很年轻,现在已经老的快死掉了。
这座监狱名字起得森严可怖,其实什么人都关,豪门里惹出是非的淫娃妖妇、市井里打架杀人的贩夫走卒、乃至一些犯了事的低阶的官员,都可能往这里扔。不过这里也是南淮城里防备最森严的监狱,关在这里的人犯的事儿都不小,隔几天就砍几个,牢房空了又填满,犯人流水样地换。当然也有像老汉这样的例外。
“说起来老哥儿你是犯了什么事儿?”年轻人捏着手心里的两枚石子儿抛了抛。
“假造金票,是杀头的罪。”对面的老囚犯倒也不很沮丧,答得很是坦然。 “假造了多少?”
“也就二十万金铢。”
年轻人愣了一下,笑出声来:“难怪是杀头的罪,你假造的金票可以买半条紫梁大街了。”
“那您是犯了什么事儿?您可是帝都大名鼎鼎的大将军,能沦落到这里来,犯的事儿不会小。”老囚犯反问,他们这些人关得久,跟外面不通消息。
年轻人抓了抓头:“说起来被抓到了把柄的事儿也就是私下里调动军队。” “调动军队?调动了多少人呐?”老囚犯追着不放。
“也就三四万人。”年轻人学他的口气。 “难怪是杀头的罪,你私下调动的人能把一国给打下来了。”老囚犯得意洋洋的报复。
两人一起笑了起来,看起来对于彼此要被杀头这个事情倒有几分欢悦。 “其实我觉得我还算运气的。”老囚犯说。 “你是说没判磔刑算运气?”
“不是,”老囚犯说,“反正我没家人,死了就死了,没什么牵挂的,这就是运气。早知道造它两百万金铢的票子出来,也还是砍头吧?”
“你倒也想得开。”年轻人笑。 “这年头四处都打仗,我看天朝也安静不了多久了。打起仗来,谁敢说自己就能活命?犯了王法的不犯王法的,刀砍过来都是人头落地。这就是乱世啊,个个都是身不由己,个个都是图口饭吃,跟讨活路的狗差不多。我就是运气差点儿。”老囚犯叹了口气。
年轻人沉默了一会儿,又默默地看向墙壁上唯一的窗,冷雨从窗外泼洒进来,外面一片漆黑。
年轻人沉默了一会儿,又默默地看向墙壁上唯一的窗,冷雨从窗外泼洒进来,外面一片漆黑。
三
天地间忽然响起一声极飘渺的琴音,只有一声,在雨夜中袅袅弥散着,就快要消失时琴声又响了起来,这次却是清晰有力的穿透了雨幕,刚劲铿锵。
“这是……”年轻人微微皱眉,话还未说出口,只听见身后也穿来了急促繁杂的马蹄声,看来是惊动了守夜的士兵。
隼面容一肃,道“将军只管走,后面有兄弟们挡着,不必担心!”他微微侧身,身后有上百个身批轻甲的精装武士,手上绑着弓弩,腰间挂着长刀“只要琴声不停城门就不会关闭……千万不要辜负了五皇子一片苦心!”
“……五皇子?”
年轻人愣了愣,抬头遥望远处高耸的城墙。
少年穿着锦织的白色广袖长袍,身披拖地的披风,盘腿坐在城头弹一把七弦的古琴,烈风吹起他披风上的一个个流苏,衣诀翩飞,在暗夜中白的耀眼。
“真是的……”年轻人苦笑“以前偷跑出宫喝酒被陛下发现时怎么没见你这样仗义?”他突然一挥缰绳,高声大喊:“走!”
“得令!”
身后的武士亦振臂高呼,策马冲锋!
天地间忽然响起一声极飘渺的琴音,只有一声,在雨夜中袅袅弥散着,就快要消失时琴声又响了起来,这次却是清晰有力的穿透了雨幕,刚劲铿锵。
“这是……”年轻人微微皱眉,话还未说出口,只听见身后也穿来了急促繁杂的马蹄声,看来是惊动了守夜的士兵。
隼面容一肃,道“将军只管走,后面有兄弟们挡着,不必担心!”他微微侧身,身后有上百个身批轻甲的精装武士,手上绑着弓弩,腰间挂着长刀“只要琴声不停城门就不会关闭……千万不要辜负了五皇子一片苦心!”
“……五皇子?”
年轻人愣了愣,抬头遥望远处高耸的城墙。
少年穿着锦织的白色广袖长袍,身披拖地的披风,盘腿坐在城头弹一把七弦的古琴,烈风吹起他披风上的一个个流苏,衣诀翩飞,在暗夜中白的耀眼。
“真是的……”年轻人苦笑“以前偷跑出宫喝酒被陛下发现时怎么没见你这样仗义?”他突然一挥缰绳,高声大喊:“走!”
“得令!”
身后的武士亦振臂高呼,策马冲锋!
百度小说人气榜
扫二维码下载贴吧客户端
下载贴吧APP
看高清直播、视频!
看高清直播、视频!
贴吧热议榜
- 1懂王又变卦电子产品还要征税1669320
- 2新海诚大赞哪吒2谁破防了1542974
- 3EDG弃用Simon内幕曝光1273972
- 4问界M7在沈阳车展现场失控1148202
- 5PS5涨价你还会买吗953784
- 6剑网3x仙剑1联动外观冲不冲678875
- 7维斯塔潘会不会离开红牛476592
- 8张艺谋新片官宣阵容你怎么看430399
- 9射雕全网上线评论区全在夸373890
- 10尹锡悦内乱案开庭结果如何352800